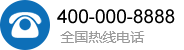天天游戏应答:本人53年出生,54年起大水,听父母讲在家中可捞鱼虾,那时也没有记性应该讲那时生活并不太穷,我家条件在村里数中等,还算可以。
但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,已有了记忆了,偶然碰到死猪死羊已是美歺,不可能扔了,大柴火煨着,放点辣子,真挺香的,可能是煨的时间长,也没见谁吃出病来,当然只能吃两口一个六口人就一小碗,能派两三块已不错了。
大人就惨了能吃的都找光了,大多数人浮肿,纯属营养不良,实在没法吃什么《观音粉》,就是一种地下的发清色的泥巴,可怜人们吃下去了,拉不出来,硬掏大便把肛门掏得鲜血直流,惨不忍睹。
大人受苦,把能吃的,米皮糠,豆饼,数量很少的,给我们小孩吃,必竟才几岁,那时也怪,连萝卜青菜都看不见,那时的老百姓很苦,而苏联又逼债,我们上初一时相对好点,一半米,一半山芋干蒸饭,有时5分钱菜汤。
以后也慢慢的好起来了,到二十岁时己很不错了,二十五岁时候就常有鸡鸭鱼肉了。
苦就苦在三年自然灾害阶段,这是难忘的回忆,能弄到米皮糠吃的,巳是很不错的了,这是本人经历,不是故事!
“红薯干、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——这句顺口溜是来自六十年代的豫东农村。红薯,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叫法,番薯、甘薯、地瓜等等叫法不一,在我们河南豫东这一带叫做红薯,由于红薯属于高产农作物,是当时城乡最主要的农产品之一。
秋日好时光我和爱人回老家(河南睢县)去了一趟,爱人看到了庄稼地里的红薯叶甚是好奇,于是就到红薯地里掐了一些,绿绿的叶子很是好看。红薯叶子有着不同的吃法,在开水里过一下,撒上一点盐就是一道不错的菜,用面粉拌一下在锅里蒸,就是很好的蒸菜,用面粉和在一起蒸成窝窝头(如图)甚是好吃。
农村的叔父告诉我们,现在种红薯的少了,因为吃的人少了,都以精细农产品为主了,睢县在五十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,基本上都是以红薯、红薯干、红薯叶为主,这一点我记忆犹新,我出生在50年代末期,小时候吃的基本上是红薯、玉米,仅仅到了春节的时候和“麦罢”(七月份刚收完小麦)才可以吃上几天“好面馍”(麦子面粉做的)。
儿时的我记忆深刻的是,盼望姑姑给人家推磨(那是没有磨面的机械设备,玉米、小麦、杂粮磨成面粉,全是靠人工推磨,研成的面粉)回来时能带来两个窝窝头(红薯面、玉米面等杂粮磨成面粉做成的),能吃上窝窝头总比整天啃红薯好吃的多,红薯叶子做成菜,再沾点辣椒粉(有时用水拌在一块)用嗮干的红薯片,即:红薯干在水里煮一下,就是当时的汤,红薯、红薯干、红薯叶是我永远不可忘记的食粮。
如今的豫东农村,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好多村民都扒掉了砖瓦房,盖起了“洋楼”,实现了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,大多村民户开上了小汽车,烧上了煤气灶,城里人使用的,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,农村一片新气象。
叔父自豪地告诉我们:现在你们城里人有的,我们都有,城里人没有的,我们也有,比如我们的农家小院,各种新鲜的蔬菜应有尽有,院子里硕果累累,挂满了枝头,吃的都是新鲜的, 你们城里人吃得到吗?
我读高中时,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为0元。但我家有粮,我爸向食堂主管恳求,用粮当菜票。我成了学校里唯一不交餐票的人。还有一人,一学期的生活费为0元,她家太穷,没钱交生活费,于是她每天偷偷地在宿舍切一片酸罗卜进餐,一个酸罗卜她要吃二个星期。很快,第二学期到了,因为我家是卖红砖的,红砖一卖出便有钱了,而我一跃成为全校最有钱的人,我一个月可以花掉其他同学一学期的生活费。但那个女的,每天还在吃一片酸罗卜,甚至连一片酸罗卜也没有。有一次,当我们在外面玩时偶遇到她,才发现她为了拿酸罗卜,踱步走30公里回家然后再走30公里来学校,每每她到学校已经是夜静人寝了。第三学期,她父母亲不让她上学了,因为交不起学费。于是由校长领头,在学校里募捐,我们也有幸来到了她家。可是,一到她家门前,门儿还没开,全场师生痛哭。士砖房,严重裂缝,随时有倒的可能!门是竹子做的,严格来说根本就没有门。瓦上面是用稻草铺了一层防漏。我们心惊胆跳地把头伸进门内向里面张望。房内乱七八糟的堆满了废瓶废胶等杂物,满屋子有股浓浓的药味。一个有点残疾的女人正在给躺在床上的男人喂药。那只半边的锅特别醒目地躺在灶台上,几件补丁衣裤骄傲地挂在竹竿上。我极力地想看看这房子有什么值钱的东西——一只半边的锅,四个碗,一张破旧的小桌子,两张木板床,三床单薄的被子,一些干净的补丁衣裤。听他们说,他家没有田,政府给了他三分地用来种菜。房子是院子里集体房,院里人不住,便借给了他们。政府也补贴他家一些钱,根本就不够用,但多半用来给她交学费了。她老爸生病,年头到年尾都得吃药。她妈妈经常去外面帮别人做些事,只为了一日三餐的粮食。临走时,所有学生都默默无言,只有校长在给她父母做保证,一定要让她毕业。学生们悄悄商议,把零用钱积攒起来,留给她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。
她学习很努力,成绩也很好。毕业那年下半年,校长可能在教育部门申请一个留校教学资格,让她去教育局考了试,她很荣幸地留下来成为一位教师。
我生于六十年代,那是家里兄弟姊妹很多,劳动力少,饭都吃不饱,更别说什么菜了,一般情况下,一年四季,吃的最多的菜是咸菜,腌芥菜、腌辣椒、腌豆角等等,遇到旱灾或水灾,自留地的菜都死了,什么菜都没有吃。
父母想尽了办法,从豆腐店搞来,用盐拌一下,放在坛子里,搁上几天,,到煮饭的时候,抓上几把,浇几滴香油,什么调料都没有,放到饭锅里蒸一蒸,就算是菜了,我们就着那的咸味吃饭,就这样的饭菜还不能够吃饱。
60岁左右的人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,国家经济困难,每个家庭都是粮食不够吃,我小的时候冬天和姐姐抬着水桶起早去豆腐房排队,不买豆腐只买,回来用大碗装满了扣在木板上,一坨一坨冻了存起来,吃的时候拿一坨化开,和萝卜或是萝卜樱或是白菜等一起放锅里加盐炒,即当粮又当菜,那时候是为了充饥。现在条件好了想吃啥就吃啥,有时候自己做豆浆,出来的豆渣还是不舍得扔,放点绿叶菜炒炒吃,现在吃是为了健康调剂一下饮食搭配。
我是一个70后,小时候跟随当兵的父亲“东跑西颠”,基本在四个城市待过。因为一般军营都比较偏僻,基本除了驻军以外,就是荒野郊区。加上那时候物资的确匮乏,加上母亲当时随军也没有工作。老家还有老人需要赡养,所以小时候的日子确实比较艰苦。
记得我家里小时候常吃的就是这道“懒豆腐”,所谓的“懒豆腐”中的豆腐,其实就是磨豆腐剩的。
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天天游戏,豆腐可是好东西,而且并不能轻易买到,需要凭票供应。而且黄豆只有家里有病人的时候,才能供应二斤。这个现在非常普通的东西,那时候还是很“金贵”的!
我妈妈随军的时候,从老家带了一个小石头磨,到现在四十多年了!我家里还保留这个东西。这个小磨在当时可立下了“汗马功劳”,老家的亲戚每年秋收的时候,大多会从邮局给寄一些黄豆和花生米。等到邮局的包裹单来的时候,是我们一家最开心的时候。
爸爸就会骑上借来的二八大自行车,有时候高兴了会带上我和哥哥,横梁上坐一个后座一个。去城里的邮局取包裹,那时候的邮局尤其一到年底,简直是“人山人海”。拍电报的、寄包裹的、取包裹的都需要排队。
老家的几个亲戚每年这几十斤黄豆和花生,简直成了我家餐桌上的美味!一般都是把黄豆或花生泡上一晚,然后加水用家里的小磨磨碎。就用这个黄豆渣或花生渣,搭配点白菜叶,熬上一锅“懒豆腐”。一人一大碗,当饭又当菜。有特有的豆香或花生的香味,要是哪天高兴了舀上一勺猪油同炖,简直就是“人间至味”。
现在我有时候想起这道菜,也会用家里磨豆浆剩下的,来搭配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来熬制。但是现在精心制作的制作的这道菜,除了入口发涩和豆腥味以外,真的吃不出以前那个味了!难道是口味变了?还是现在的黄豆不行了?
关于用儿时的一道菜,来证明小时候家里很穷,我觉得就是这道“懒豆腐”。大家有吃过的没有?感觉怎么样?欢迎留言、评论!
自我记事起,就感觉到我们家条件不及周边邻居家。住的是租来的两间民房,家徒四壁,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,是一个废弃的木制包装箱。六个人挤在一个炕上,我和姐姐打通脚(就是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)合盖一条被子,穿的衣服是大人衣服改制的。姊妹四个大小两岁,到了发育的年龄,粮食指标就不够吃了,红薯干红薯面成了替代品,每每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吃玉米面窝头,就馋的直流口水。
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国营小饭店,由于地处邯临路的主路,当时全县城只有三个国营饭店,所以吃午饭歇脚的人很多。有一年夏天的一天,看到邻居家的小朋友端着脸盆,里一面盛着西瓜皮,高兴的往家走,我问她从那里拿的,她说是检的。我跟在她后面,到家后,阿姨把没吃净的瓜瓤分离出来,给我们吃,我不好意思吃了一小块,很好吃。
回到家,和妈妈说我也要捡西瓜皮,妈妈说:可以捡来做菜吃,但不能吃别人吃剩的爪瓢,不卫生!我口是心非的答应了。醉翁之意不在酒,心想,不吃瓜瓤我捡瓜皮干嘛。吃过午饭,拿着洗脸盆,去饭店门口捡瓜皮。有好几个小孩也在捡,东一快西一块的往盆里放,苍蝇乱飞,看着太脏,我一块也没捡。我拎着盆子转游,看到不远处有个卖西瓜的,几个拉脚的伯伯在旁边挑瓜,我急忙赶过去,跟着买瓜的人,他们找了个阴凉的地儿,把两个西瓜打开,我急忙把盆放到他们中间,有一个伯伯说:这小姑娘还真有眼力架!他们把吃过的西瓜皮,都扔到我的盆子里,伯伯拿一块西瓜让我吃,我揺摇头,其实当时口水直在嘴里转。瓜吃完后,伯伯把给我我没吃的那块,也放到了盆子里,我说了声谢谢,端起盆子就往家里走,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……。
到家后,我急忙拿起那块瓜吃了,好甜,还想吃,就把西瓜皮用水洗了洗,用小勺子把剩余的瓜瓤刮出来,放到嘴里慢慢品尝,简直就是美味!过去吃剩的西瓜皮,啃的很干净,两个西瓜也刮不出一碗瓜瓤来。晚上妈妈下班回来,看到我洗的干干净净的西瓜皮,还夸了一句勤快,妈妈把瓜皮加料煮熟,晾干,再用葱花把瓜皮炒香,太好吃了。
当时运输不发达,都用人力车拉东西,拉车的人简称”拉脚的”。他们风餐露宿,穿的衣服都看不出颜色了,看着哪儿都是黑黑的。从小就爱干净的我,却能吃他们剩的东西,这应该就是饥不择食吧!
斗转星移,一切在变,但西瓜皮做咸菜一直是我的最爱,每到夏天,只要吃到厚厚的西瓜皮,我都会按妈妈的方法做成咸菜,百吃不厌。
爸爸在外地工作,吃“国家粮”,是“革命干部”。妈妈农村户口,是“亦工亦农”职工,在乡供销社工作,也有少量工资。
我胆子大体质好,上山吸茶花蜜,窜茶树上摘茶泡茶舌,下河游泳,没事紫云英田里打个滚,顺便再捅捅供销社院角落放的蜂箱,想偷点蜂蜜吃。能吃能睡,脾气火爆。
妹妹和我不同,什么都跟我相反。说话细声细气,温柔胆小乖巧可爱。爱笑,体质弱,光生(漂亮)。
我长的很平常,虽然白皮肤大眼睛,但五官不出众。妹妹则不同,从小就是美人胚子。
我长得像我爸家的亲戚,我妹妹长得像我妈家的亲戚。我们姐妹俩长相迥异,陌生人总不相信我们是亲姐妹。
我外婆是十里八乡的大美人。我妈很小时候,外婆就过世了。乡里说外婆早逝,是因为太漂亮了,红颜薄命,“光生(漂亮)夭寿”。
妹妹乌黑柔软的天然卷发,皮肤吹弹可破,五官深邃。小嘴红红的,睫毛长长的,真人版的洋娃娃,还是个“新疆(尔族)”洋娃娃。妹妹温柔爱笑,人见人爱,谁都喜欢抱她,赶场的人偷偷看她。
但,妹妹身体不好,体质弱。动不动就感冒发烧拉肚子,吃药还没用,非要打吊瓶。
我们早吃完饭了,她还愁眉苦脸坐在小桌边,拿着筷子,慢慢数着饭粒,碗里的饭没见少。
老妈怕猪肝没炒熟,妹妹吃坏肚子,猪肝炒的老,木渣渣的,实在不好吃。猪肝本身很腥,无论放多少调料,葱姜蒜辣椒花椒齐下锅,还是腥。
可怜的我,食之难吃,弃之可惜。闭着眼屏住呼吸,快速把一大盘热腾腾腥乎乎木渣渣的猪肝吃了。
我也采取过措施的,在我妈没看见的地方,悄悄威胁过妹妹,要她下次说想吃炒腊肉蛋卷子酸辣小鱼干什么的。
妹妹平时干不过我,这是她报复我的绝佳好时机,所以,无论我怎么威胁,等老妈问的时候,她又坚定喊着要吃猪肝。
(妹妹现在很好,变成了吃货,特爱吃,还长不胖。身高一米六,体重九十,身材窈窕。娃娃脸白里透红,很年轻的样子。美人就是美人。)
我是湖南人,父母吃辣。每次炒菜,先不放辣椒。炒好了给我夹出几筷子,再放辣椒炒,父母吃。
走亲戚,好吃的菜都辣。父母会给我倒半碗白开水,把肉放到白开水里涮去辣味,再给我吃。
半信半疑尝了一小片,绿绿的辣椒吸了油,很润泽,咬一口软软的香香的,可承受的微微辣,不但不难吃,还很好吃呢。
(网上这张图片,五官神态很接幼年的妹妹,纤细呆萌,连头发都像,蓬松微卷)
苦累菜是小时候春末夏初吃的一道菜,我生于七十年代初,小时候基本上能吃饱饭了。玉米面是主食,白面很少吃,整年不见荤腥。菜饭单调,到夏末槐花盛开之季,跟着哥到野外槐树上钩槐花,由于我小上不了树,只能看着哥哥们花树上吃饱了,才往树下钩槐花我才能吃到。钩够一篮子后回家。到家后母亲清洗一遍槐花,用玉米面拌上槐花加盐再加少许油,上笼屉蒸。大约半小时后出锅,由于玉米面没有粘性不成型,只能盛到碗里吃,加上几滴酱油,那真是童年最好的美食了,此菜饭名叫苦累,不知是谁起的名,寓意非常好。
我说的这道菜确切的来说她不是一道菜,而是一种用蒜臼子捣鼓的蒜味佐料汁。相当于现在人们去火锅店自配的调味碗底。
直到现在,这道调味小菜还广泛性存在,它和窝窝头,玉米面馒头等忆苦思甜的食物不同,因为它很有味道。
这道调味小菜广泛存在苏鲁豫皖交界地,制作方法非常简单,就是把大蒜,青辣椒放在蒜臼里捣碎,加入食盐,酱油,麻油鼓捣成酱汁。
制作方法上非常简单,甚至连青椒都不用放进蒜臼容器。只用大蒜子鼓捣成酱汁。
这个以大蒜为主体的酱汁可以用来吃面条,除了这个酱汁什么菜都不用放。例如在夏季,面条煮好之后过完凉水捞出,然后直接把酱汁码在面条上拌着就开吃了。
家里宽裕一点的,除了放点黄瓜丝,然后就放点芝麻酱。值得一提的是,是芝麻酱,而不是花生酱。
这个酱汁儿除了可以吃面条儿之外,可以卷着烙馍,就着馒头吃。在那个年代,这个东西非常下面,下馒头。
大蒜也只有在蒜臼里鼓捣种酱汁儿,才能充分发挥大蒜真正本味和浓郁的大蒜香。
这种吃法是苏鲁豫皖地区特有的吃法,用陶土做的蒜臼,配上一根圆柱体木棍,就是把大蒜做成蒜泥的神器。这个东西现在还广泛存在。
用刀背把大蒜拍成蒜泥,和用蒜臼容器捣鼓出来的蒜泥味道是两个味道,大家可以试一试。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它可以满足人的味蕾,在物质不缺乏的现在,它可以当做一个小菜品,或者让自己的凉拌菜提升一个档次。
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北方广大农村地区其实很少吃肉,有时候两三个星期赶一次集才买一次肉。
说句实在话,现在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,年龄在50岁左右的农村人,吃不吃肉都可以。有,也可以吃,没有,日子也可以过。
这个地区的人对蒜臼子,这个家常捣蒜容器,根本不陌生。提起它,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怀旧。
尤其是用它来捣鼓蒜泥,那绝对是怀旧的画面扑面而来,蒜香扑鼻。这个东西也是苏鲁豫皖地区日常生活中烹饪调味工具的象征,也是区域生活象征。
苏鲁豫皖交界地区,其实经济并不发达,现在还行。而30年前挨家挨户要饭的人非常常见,三天两头能吃肉的人家,已经算是大户了。
然而蒜汁面条儿,现在依然有人吃。就算不加任何浇头也好吃,当然如果加了黄瓜丝和芝麻酱,而且是手擀面的话,那就更好吃了。穷,并快乐着,也很好。